屈指算来,它离开世间已有几十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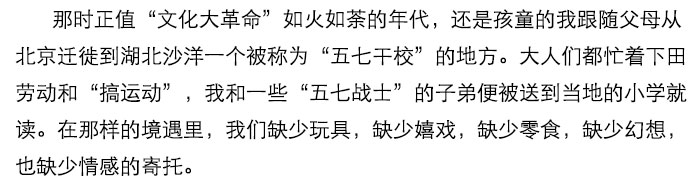
学校的课程也如我们的生活一样平淡无奇,单调乏味。然而有一天,一个农家子弟忽然在课间问我:“你要小狗么——刚满月的。”
“要。”我毫不迟疑地答。
后来他把小狗抱来了。那是一只耷拉着耳朵、长着四条短腿、走起路来步履蹒跚的小板凳狗。我不免有些扫兴,因为我很想拥有一只看起来凶狠一些的狗,就像与干校比邻的一个军人农场豢养的如同小牛犊似的看门犬一样——那狗远远看去就令人毛骨悚然。
尽管如此,我还是把小狗带回了家。由于小狗浑身都长着黑色的短毛,模样又平庸,于是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乌鸦。
邻居家的大妈说:“这狗太小,恐怕还没断奶呢!”可是我到哪儿去找牛奶或者奶粉之类的奢侈品呢?我能给小狗提供的只有从食堂打来的菜汤和米汤。
第一个夜晚,乌鸦几乎整夜都没有平静,高一声低一声的一直哀嚎到天明。许多年后我才明白,那其实是它离开母亲与伙伴后所发出的一种悲凉和孤独无援的叫声。
慢慢地,鸟鸦适应了陌生的环境。它对人很友善,不管是谁叫它,它都会循声而去,而且使劲摇动尾巴,以示友好与热情。当然,它更听从我这个主人的呼唤。
我家住在家属区最外边的一排平房里。房舍前没有围墙,只有一块空地——家家几乎都在那里开垦,并种下蔬菜、向日葵之类易于生长的植物;然后便是一条土路斜插进一片密密匝匝的小树林里。
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到不见星月的夜晚,我走出家门,面对那片黑黝黝的小树林,常会产生一种恐怖的联想。何况干校所在之地先前曾是劳改农场,在它周围仍有一些劳改队没有迁走,让人不由得把犯人与教科书以及电影、连环画中的坏人的形象连在一起,我认定他们在黑夜里会露出狰狞的面目。但是自从有了乌鸦之后,我的胆子明显壮大了。当我晚上出门时,它总是蹦蹦跳跳地陪伴在我左右。虽然它那么矮小,瘦弱,几乎经不住人们的一脚,可我仍觉得它比手电筒要有用得多。
乌鸦还为我和伙伴们乏味的上学路途增添了乐趣。许多个早晨,我们都要带着它走上一程。学校离我们居住的地方有几里路,其间还要经过一道灰黄色的沙丘。不知大自然是如何修筑的那道沙渍的堤坝,它绵延伸展,一眼难以望到边际。沙丘上寸草不生,而它的两边却是葱郁广阔的田野。每当走上沙丘,乌鸦便如同挣脱枷锁似的尽情奔跑,甚至嬉戏般地追逐落在那上面的麻雀、八哥或是别的什么鸟类。有时它会跑出很远,直到我们吹起尖厉的口哨才气喘吁吁地狂奔回来。而后我们对它说:“乌鸦,回去!”于是它悻悻地转回身,一副不情愿的样子。不过当我们走下沙丘很远了,回过头去遥望时,往往发现它仍蹲坐在沙丘上,一动不动地默视着我们??
在“五.七.干.校”中,一分钱买两块儿的水果糖对一个孩童来说,差不多算得上珍馐了。然而为了训练乌鸦能听从诸如“趴下”、“滚儿一个”之类的口令,我几乎花去了好几毛钱。虽然乌鸦绝不像马戏团那些哈巴狗一样聪明伶俐,但是对于生活中少有快乐的我和伙伴,甚至邻居家的大人们来说,乌鸦所能做的一些简单动作毕竟能让人笑逐颜开了。
乌鸦渐渐长大了,本能地担负起保护主人以及我们这排宿舍的职责。每当有陌生人在那条紧靠树林的土路上出现,它都会警觉地注视。如果那人跨进它所戒备的地域,它就要发出一长串激烈的狂吠声,甚至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有时我跟伙伴们做些摔摔打打的游戏,乌鸦也在一旁又蹿又跳,不失时机地助我一臂之力。尽管如此,我却从未见它真正凶狠地去撕咬过哪个人。记得那时我相当引以为骄傲的一件事就是,伙伴们向新来的伙伴介绍说:“乌鸦就是他家的。”
光阴在迷离恍惚中悄然流逝了。又到了冬天的时候,乌鸦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邻居家的大妈说:“它怀上了。”我却不以为然,因为在我眼里,乌鸦还是一只没有长大的狗。
终于有一天,我放学回到家,邻居兴奋地告诉我:“乌鸦生小狗了!”我急忙跑到院中用厚厚的干草盖顶的狗窝边,看到四只胖乎乎、还没睁眼的小狗崽儿正围着乌鸦爬来爬去。乌鸦则疲惫地卧在地上,不时用舌头舔舔身边的孩子。
一连几天,明显消瘦下来的乌鸦总是守在窝外,用身体挡住出口,不让陌生人靠近。
那一年冬天非常冷。尽管没有下雪,但淅淅沥沥的雨水飘落下来很快就结成了冰。我们的屋里没有暖气,只有一只用黄泥做成的小火炉发出微微的热量。一天夜里,我冻得睡不着,只好眼巴巴地望着仅仅铺了一层草席和一层薄瓦的屋顶。屋外,寒风呼啸,吹得裹着冰凌的树木发出一阵阵喀啦喀啦的响声。
忽然,我听到门外有一阵的响动,不久,门板上就响起了轻轻的沙沙声。我听得出那是乌鸦在挠门,于是急忙裹起大衣跳下床,悄悄把门打开一道缝。一股寒气直钻进来。朦胧中,我看到四只小狗紧紧挤在乌鸦身边,发出吱吱的叫声。乌鸦则仰头看着我,似乎在乞求什么。也许它们太冷了。我想着,把门又开得大了一点儿。四只小狗显然感觉到了温暖,争先恐后摇摇晃晃地往屋里钻。等小狗们都进了屋,乌鸦才冲我摇了摇尾巴,然后像往日一样卧在冰冷的砖石上。
那一夜,乌鸦一直守在门外。而四只小狗则围着小泥炉睡得安安稳稳。
自那以后的许多年里,我笃信了人类给予狗的那句溢美之辞——狗通人性。不仅如此,在全力保护以及怜爱后代这一点上,狗与人类显然也是相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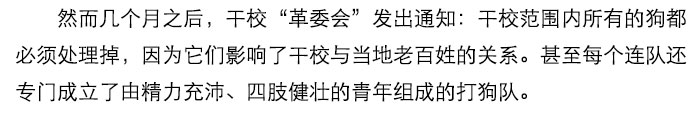
许多狗被消灭了,但是乌鸦仍然在逃。父母反复劝我说:“把乌鸦交给打狗队吧。”而我只是说:“让他们去打呗,我又没拦着。”其实据我所知,乌鸦有两次已经陷入重围,可最终还是逃脱了。
也许乌鸦明白处境危险了,一连好几天它都没有回家。我担心它是让打狗队给捕获了。然而一天傍晚,当我忧心忡忡地吹起口哨之后,乌鸦竟风风火火地从前面的小树林里跑了回来。它喘着粗气,使劲儿对我摇头摆尾,还不时发出吱吱的哼叫声,像是述说它的委屈与惶惑,又像是乞求我的怜悯与安慰。
而我能对它说什么呢?
我只能把它藏在床下,告诉它:“千万别再出去乱跑了,免得被人看见。”
可惜,乌鸦还是被发现了。第二天,干校一个连队的负责人找到我,询问乌鸦的事。尽管我申辩说乌鸦从没咬过人,尤其是当地的老百姓,但那人却说:“这不是咬人不咬人的问题,而是??”
年少弱小的我到底还是屈服了。
当看到打狗队的青年摆出胜利的姿态用绳子拖走乌鸦,而它仍奋力挣扎着回过头用无助的眼神望我的时候,我的眼泪忍不住扑簌簌滚落下来。
当晚,食堂恰好改善伙食,其中有一盆我曾梦寐以求的佳肴——红烧肉。但是,在听说那里面掺有乌鸦的肉后,我看也没看一眼便扭头离开了。
那天,我没吃晚饭??
在历史的长河里,几十年似乎只是短暂的一瞬。如今,有时我走进玩具商店,看到柜台上那些造型可爱甚至能摇尾狂吠的玩具狗时,每每会生发一种感慨:或许有朝一日,玩具商们可以制造出更逼真更形象乃至装上电脑听得懂人类语言的狗,但是,他们无法再现曾经活在人情冷漠年代的那只狗——那只叫做乌鸦的狗。